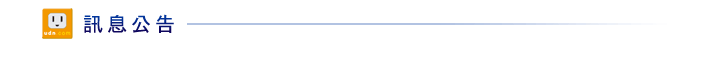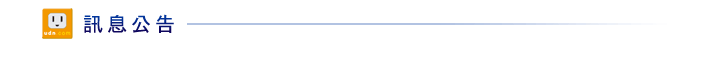| 一則簡訊 我是不是害死了自己最好的三個朋友,每個人的觀點不一。 如果你問布雷克•羅伊的外婆貝西奶奶,我想她會說不該怪任何人。那是因為今天稍早她第一次看見我的時候,便把我緊緊摟進懷裡,含著眼淚給了我一個大大的擁抱,並且在我耳邊輕聲說:「卡佛•布吉斯,你不必為這件事負責,上帝知道,我也知道。」貝西奶奶心裡想什麼就說什麼。這就是她的意思。 如果你問艾里•包爾的父母,皮爾斯•包爾醫師和瑪莉莎•魯賓•包爾醫師,我想他們會說可能是我。今天當我看見他們時,他們都目不轉睛的看著我,並且和我握手。從他們的面容,我看見的失喪之情多過忿怒,從他們虛弱無力的握手中,可以清楚感受到他們深沉的憂傷。而且我猜得出來,他們或多或少也會把自己所失去的歸咎在我身上,所以他們才會說可能是我。那麼,他們的女兒,就是艾里的雙胞胎姊姊艾達爾呢?我們以前也是朋友,但不像艾里和我的關係,只是普通朋友。我敢說,從她對我怒目而視的神情,已經「清楚明白」的表達了她希望我也在那輛車子裡。這是幾分鐘前才發生的事,當時她正在和我們班來參加喪禮的同學說話。 再來就是費德瑞克•愛德華法官和他的前妻辛西亞•愛德華。如果你問他們,是不是我害死了他們的兒子佘古德•馬歇爾•愛德華(我們都叫他「馬斯」),我想你會聽見很肯定的「可能」兩個字。今天見到愛德華法官的時候,他一如以往,衣冠楚楚像座高塔般的矗立在我面前,我們好一陣子都沒有開口說話,我們之間的空氣就像石頭一樣粗鄙僵硬。「先生,見到你真好。」我終於伸出流汗的手開口說。 「沒什麼好的。」他的聲音威嚴,下顎肌肉緊繃,仰起頭看著遠方,像是在說服自己相信,我不過是個微不足道的角色,也可能是在說服自己相信,我和他兒子的死沒有關聯。他和我握了握手,感覺像是在執行公務,也像是在表達,這是他唯一能傷害我的方式。 最後,就是我了。我會斬釘截鐵的告訴你,我的確害死了自己三個最要好的朋友。 不是故意的。我十分肯定沒有人會認為我是故意的;就像我在一個死寂的夜晚溜進他們的車子底下,切斷了煞車線似的。我沒有那麼做,只是殘酷又諷刺的是,我是用寫的,就這麼把他們的人生寫出了這個世界。「你們在哪裡?快回我訊息。」不是什麼特別又有創意的訊息,但是他們找到了馬斯的手機(當時開車的人是他),裡面有一則寫了一半要回覆我的訊息,正如同我所提出的要求。看起來彷彿他正在打簡訊的時候,以七十五英里的時速,一頭撞上在高速公路怠速停止的聯結車後面,整輛車就這麼鑽進車子底下,連車頂都被削掉了。 是不是因此就能確定,這一連串導致我朋友死亡的事件是肇因於我傳的訊息?沒有辦法。可是我自己心知肚明。 我像個行屍走肉,茫然又空洞。雖然還沒有椎心刺骨的劇痛,但我相信,在未來不斷開展的日子裡,時而乍現的痛楚一定在等著我。就像有一回我在廚房裡幫媽媽切洋蔥,菜刀突然一滑,就在我的手上劃開了一道傷口。我愣怔了一下,彷彿我的身體需要明白自己被劃了一刀。頓時我明白兩件事:一、我只覺得自己被猛然一擊,感覺到脈搏微弱的跳動,但沒多久,疼痛感便如排山倒海而來。 喔,好痛。二、我也在頃刻間驚覺,自己的血正汨汨流滿了媽媽最喜歡的那塊竹製砧板(沒錯,人和砧板可以建立非常深厚的情感;不,我也不知道,因為我從來沒問過)。 於是,我坐在布雷克•羅伊的喪禮中,等待痛楚襲來。等著讓自己的血液開始流遍所有的事物。 文章出處/資料提供:台灣東方 |